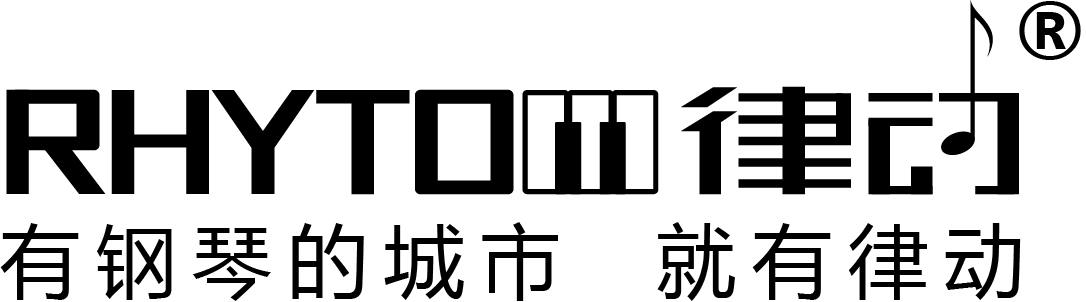今年8月22日是偉大的法國作曲家克勞德·德彪西誕辰150周年,然而音樂界仿佛不約而同地在回避這個日子。粗略地統計一下,全國各地舉辦的紀念德彪西誕辰專場音樂會屈指可數。相比前年肖邦的兩百周年誕辰時,大街小巷處處可聞鋼琴聲,音樂廳里每晚鋼琴必然奏響,夜曲與波羅奈茲輪番上演,熱鬧非凡,連波蘭大使都感嘆說中國的紀念肖邦音樂會比波蘭本土還要多;又相比去年古斯塔夫·馬勒百年忌辰,僅北京上演的專場音樂會就有20余場,這位曾言道我的時代終將來臨的奧地利人盡管有著預言家的先見之明,但未必能料到他的聲名會在百年之后遠播到重洋以外的中華大地。
也難怪,古典音樂在中國普及開來的時間太短,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并不很多,因此能在紀念日時得到特殊禮遇的作曲家也少得可憐。不過即便如此,德彪西也應該名列其中。這位出生于巴黎西郊圣日耳曼昂萊的瓷器店老板之子,年輕時有幸跟隨肖邦的一位弟子學習鋼琴,后來進入了久負盛名的巴黎音樂學院學習。1880年,18歲的德彪西遠赴俄國,給當時有名的貴婦梅克夫人當家庭鋼琴教師——梅克夫人同時也是柴可夫斯基的老師,但遺憾的是兩位偉人并沒有見過面。據說,梅克夫人把德彪西寫的一首鋼琴小曲《波希米亞舞曲》交給了柴可夫斯基,但當時已名滿天下的柴氏回應得不冷不熱,這首曲子很好聽,但是太短了。沒有一個樂思是展開充分的,結構也不完整,全曲缺乏統一性。
令這位在柴可夫斯基眼里才華平平的年輕作曲家命運改變的是兩件事:其一是欣賞到了瓦格納的歌劇,其二是理解了印象派的繪畫。瓦格納整體藝術的觀念盡管用來表達屬于德意志民族的情感,但也令這位來自法蘭西的年輕音樂家極為震撼,對他造成的影響也持續一生;而當時流行于法國的印象派繪畫及文學更是令德彪西開創了全新的音樂流派——印象樂派。從他的《牧神午后》、《大海》與貝加馬斯克組曲中《月光》這些膾炙人口的作品里,聽眾倘若閉上雙眼,一定不難聽出那些搖曳的光影與色彩,斑斕的色塊仿佛在眼前變幻。與同時代的另一位印象派大師拉威爾相比,盡管德彪西的音樂少了幾分精確犀利,但聽起來毫無侵略性,更能給陌生聽眾以親近的感覺。
德彪西一生都在追求真愛,他與很多女人陷入過持續多年的苦戀,曾與一位巴黎的時裝模特結婚,但因嫌對方不懂音樂棄之而去。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他遇到了一位已身為人婦的歌唱家,與她私奔到了英國,這導致晚年的作曲家眾叛親離。返回巴黎后,兩人生下了一個名叫秋秋的女兒。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德意志帝國發起了猛烈的魯登道夫攻勢,德彪西就在這一年的3月25日死在了巴黎城中隆隆的炮聲里。在作曲家的一周年忌日后不久,他唯一的孩子秋秋也被白喉病奪去了生命。德彪西創作了無數動人的樂章,但倘若聽者不去仔細分辨曲中之意,又怎能聽得出作曲家心中的寂寞?